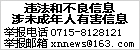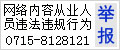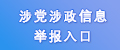亲情印记
半个世纪的光阴无声地滑过,那感觉有点像无声电影。虽然无声,却有形。形在哪里?——皮肤上留下了许多岁月的印记。那些印记深深浅浅,大小不一,往俗里说其实就是疤痕,似乎有些有碍观瞻,但我却一直并不在意。因为,它们留给我的不是伤痛,而是一段段隐藏在岁月深处的温馨记忆。
最早的一道亲情印记,是童年时代留下的。在右臂外侧,大约一厘米长,三毫米宽。这是二哥留下的印记。那时候,二哥已上学,我还在田野撒欢。那天傍晚,二哥放学回来,爸爸派给他一项工作——跟他一块削竹筷子。爸爸不知从哪里捡回一些竹棍,用柴刀削成筷子,爸爸一个人忙不过来,就叫二哥帮忙。我从外面玩耍回来,看到爸爸和二哥削竹筷,感觉挺好玩的,便主动要求加入,也拿起一把镰刀学着削竹筷。突然,二哥一不小心,用力过猛,手里的镰刀尖滑到了我的右臂上,顿时划破了一道血口子,鲜血直流。我有些懵了,也不知道疼,只是看着流血的伤口发懵。爸爸立刻用火柴皮帮我贴住伤口止血,一面责骂二哥怎么不小心。我看二哥垂头丧气被骂得可怜,十分不忍地央求爸爸说:“二哥不是故意的,我也不疼,您别骂他了!”后来,那个地方便留下了一道永久的疤痕。那部位别人一看,都以为是打疫苗留下的痕迹,只有我知道,那是我身上第一道亲情印记。
右脚背上一道浅浅小小的疤痕,是我少年时和小妹上山砍柴留下的印记。那一年,我家刚从平原搬来鄂南山区,对于砍柴这活儿很是陌生。但村里像我们这样的半大人儿都担负砍柴的工作,我和小妹的节假日便大部分都在从事着这项艰巨的任务。山里砍柴用的柴刀刀背很宽,很厚,比平原地区用惯的镰刀笨重许多。刚开始时我们怎么也使不习惯,为了学会使用柴刀,我们交了不少的“学费”。这“学费”便是血。有一次,小妹的柴刀在割毛竹的时候滑到了她的左手中指上,顿时血流不止。伤好以后,中指中间的指节便永远多出了一个小肉团。又一次,我的柴刀砍到了自己的右脚背,也是血染山林。每次受伤后,我们都会为对方心疼、着急,体贴地主动多帮对方干活,让伤者好好休息,姐妹间倒比平时更多了一些温馨的关爱。
最大最明显的这块疤痕是十年前做胆囊切除术留下的。病中的各种痛皆已淡忘,但永远记得刚刚做完手术出来,一大群子侄甥女们团团围在手术室外迎候我的那一道道关切的目光;永远记得小妹在推我回病房的时候,看着我麻药未醒,止不住为我默默流泪的面孔;永远记得一向怕坐车的妈妈在得到我手术的消息后,不顾年迈体弱,风尘仆仆地从几百里外的老家直接赶到我病床边的憔悴而担忧的神情……
正因为有着这些关于亲情的鲜活记忆,所以从不嫌弃这些疤痕,相反,它们让我不论何时何地,随时都能想起亲人,忆起那些温暖的旧时光,从而心生幸福和感恩。(万红英(市直))
编辑:Administrator
① 凡本网注明"来源:咸宁网"的所有作品,版权均属于咸宁网,未经本网授权不得转载、摘编或利用其它方式使用上述作品。已经本网授权使用作品的,应在授权范围内使用,并注明"来源:咸宁网"。违反上述声明者,本网将追究其相关法律责任。
②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咸宁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传递更多信息,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
③ 如因作品内容、版权和其它问题需要同本网联系的,请在30日内进行。

娱乐新闻
-
人艺“经典保留剧目恢复计划”开篇之作 《风雪夜归人》4月25...
 2025-03-27
2025-03-27
-
摘下神探滤镜 《黄雀》讲述充满“锅气”的人物和故事
 2025-03-27
2025-03-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