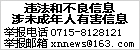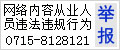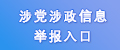门前又响爆米声
■聂松彬(赤壁)
下班回家,刚走到小区门口,一声“砰”的爆炸声越过耳际,我循声一看,一辆三轮车上火焰熊熊,一位师傅正在爆米花,一声巨响后,袅袅的青烟弥漫着稻米的清香。
我俯身抓起一把爆米,诱人的芬芳馋得我探出舌头,香脆的爆米融进我的唾液,瞬间,一缕甘甜轻轻流入我的心田。
小时候能听到爆米花的声音一般都在春节前夕。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农村哪有钱给小孩子买零食?爆米花倒成了小孩子们的最爱。每到年前,总能看到爆米的师傅肩挑货担走村串户来到家门口。当村子里传来一声声如爆竹的巨响,我立刻跑回家,缠着母亲去爆米花。那时候爆米花不像现在只出钱就行,记忆中是要自己带米(一锅一升米)和柴火的,师傅只管每锅收取2角钱的工钱。要知道那时候的一升米可是我们一家七口人的一顿饭,但妈妈居然会答应我的要求。于是,我立马将干树枝砍成筷子长的一段段,装在竹篮里,跟着母亲大摇大摆地来到村东头的禾场上排队。
深冬的乡村夜晚干冷干冷的,弯弯的月亮慢悠悠地挂在东头的皂荚树上,清冷的月光似洁白的纱巾披在禾场的草垛上,又如碎银洒在每一个人的身上。看着排在前面的小伙伴得意洋洋地提着沉甸甸的爆米袋子回家,我总是按捺不住一次次站起来挨个数着前面排队的人数。不过,每当看到爆米花的师傅停下转动的机器,双脚抬起准备蹬开爆米机时,我们连忙双手捂着耳朵站到一边或者趴在地上, “砰!”深冬的夜空如一声春雷响起,伙伴们就像春归的燕子蜂拥而上一起扑向机器旁边——地上好多爆米花成了我们争抢的零食。
终于轮到我家了!爆米机昂起头,笑呵呵地张开圆形大口,师傅接过妈妈手中的一升米倒进去再用两个指头摘了几粒糖精,然后用一根雪白的铁棒拧紧机器的盖子。师傅坐下来,一手拉着风箱一手转动爆米机,风箱呼啦啦的响,火苗滋溜溜地蹿,妈妈的脸颊通红了,皂荚树上的半边月亮也红了。这一夜,我们五兄妹每人的床头都有妈妈给的一大捧爆米花。我们趴在被子里吃着甜津津的爆米花,梦里,我的爆米花开满了村头的那棵皂荚树。
一升米的爆米花倒出来差不多有满满一大盆,母亲是位居家过日子的人,她哪舍得把这么多的爆米全部给我们当零食,等我们解馋后她会留下大部分爆米用袋子密封好,留到小年那一天磨豆腐后再做豆腐坨。腊月二十四,我们五兄妹打扫卫生,母亲和父亲大清早就出去磨豆浆,中午厨房里白花花的豆腐正冒着热气。吃过午饭,母亲便把先前准备好的爆米倒在一个大脚盆里,然后掺合适当的豆腐、姜末、香葱和盐,再把我们一个个吆喝过来捏豆腐坨。我边捏边数,盘算着等会儿自己可以吃几个,虽然双手冻得通红,但看着一排排摆放整齐的豆腐坨似乎正冒着热气,溢着豆香,我的口水都要流出来了……
“嘭!”我从一声巨响中醒悟过来,连忙掏出五元钱买了一小袋爆米花提在手上。然而,时光荏苒,这一提竟然拽走了我半个世纪的轮回,如今,村东头那棵古老的皂荚树已是枝繁叶茂,月亮还会挂在高高的树枝上,但母亲不在,爆米花再甜,也吃不出小时候的那种味道。
编辑:Administrator
① 凡本网注明"来源:咸宁网"的所有作品,版权均属于咸宁网,未经本网授权不得转载、摘编或利用其它方式使用上述作品。已经本网授权使用作品的,应在授权范围内使用,并注明"来源:咸宁网"。违反上述声明者,本网将追究其相关法律责任。
②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咸宁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传递更多信息,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
③ 如因作品内容、版权和其它问题需要同本网联系的,请在30日内进行。

娱乐新闻
-
人艺“经典保留剧目恢复计划”开篇之作 《风雪夜归人》4月25...
 2025-03-27
2025-03-27
-
摘下神探滤镜 《黄雀》讲述充满“锅气”的人物和故事
 2025-03-27
2025-03-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