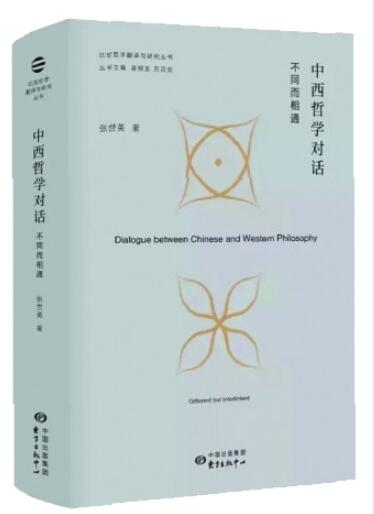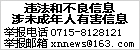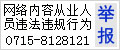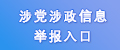相关新闻
-
积极进取忌自满 —— 读《论语》有感
《论语·子罕》载:子曰:“衣敝缊袍与衣狐貉者立,而不耻者,其由也与?为此,孔子希望子路不要止步于“升堂”,更要“入室...
-
自私·私自
最近,听了一堂廉政党课。但是,授课人赢得了热烈的掌声,收获了认同的共鸣,彰显了亲民的魅力。以其本人对动物性、人性、党...
-
新书荐读
《深刻认识新时代新思想》何毅亭著内容简介: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新时代·新思想》,从开辟马克思主义新境界、开辟中国特色社会...
-
雨天书茶
曹轩(黄石)细雨绵绵,空气润泽而温馨,清茶一盏,诗书一本,便是最好的读书境界。很喜欢在这样的环境里去读书,读一本白音格...
-
读懂时代,从读懂语言开始
日常语言影响着个体的思维方式,方言维系了民族的历史记忆,政治语言决定了国家的现实意识。”但人们用这两句话时,落脚点往...
-
齐心协力共交流 听课评课促成长 博苑书香幼儿园听评课活动
“松鼠的尾巴像什么?老鼠的尾巴长什么样?”近日,博苑书香幼儿园在华丘琪园长的带领下,进行了十一月为期三周的听评课活动,中...
-
期盼有阳光的日子
陈怡升(咸安)春雨从新年起,就一个劲儿地下个不停,身上都好像长了霉菌一般,浑身不自在,人们期盼有阳光的日子。我期盼着...
-
从汉字及汉字所记录的先秦文献中窥见中华思想、原则源头 ——...

中国“大一统”的理念追求,基本上是以汉语汉字的传播使用与统一为其底色与表征的据比较保守一些的估计,汉字可能在公元前十...
-
文字的美
黎洪涛(市直)多年前,我站在书店的二楼,外面是初夏的午后,蝉鸣声声,时间襁糊一样黏稠而缓慢,极似那简单、干净、美好的过...
-
对话莫言:扎根生活 讲好故事
扎根生活讲好故事(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纵横谈)核心阅读一个文学家首先是一个对本民族语言做出贡献的语言学家,他丰富了我们...
① 凡本网注明"来源:咸宁网"的所有作品,版权均属于咸宁网,未经本网授权不得转载、摘编或利用其它方式使用上述作品。已经本网授权使用作品的,应在授权范围内使用,并注明"来源:咸宁网"。违反上述声明者,本网将追究其相关法律责任。
②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咸宁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传递更多信息,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
③ 如因作品内容、版权和其它问题需要同本网联系的,请在30日内进行。

娱乐新闻
-
人艺“经典保留剧目恢复计划”开篇之作 《风雪夜归人》4月25...
 2025-03-27
2025-03-27
-
摘下神探滤镜 《黄雀》讲述充满“锅气”的人物和故事
 2025-03-27
2025-03-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