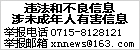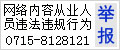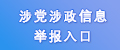母亲的命

万致婷
母亲走了,刚刚过完95岁的生日。走得很安详,走得也很满足,大儿子和大媳妇、二儿子和二媳妇、女儿和女婿都在身边。
我们把母亲的骨灰送回了黄沙铺,葬在了父亲的坟旁。
转了一大圈,母亲又回到了黄沙铺,这真是母亲的命啊!
母亲从小在汉口铜人像的仁和街长大,解放初同父亲一起来到通山,是解放后孝感卫校首批护士班的学员。从我记事起,母亲与父亲吵得最多的就是要离开黄沙铺,离开这个鸟都不拉屎的地方,要回武汉去。
武汉是回不去了,母亲先将大哥送到了武汉,和外婆、舅舅生活在一起;到了二哥出生的时候,户口已经无法落户武汉了,看到二哥小小的人儿每天只能站在田埂上与牛玩耍,免不了又与父亲争吵起来。吵来吵去,母亲在黄沙铺终究还是呆了20多年。
我是在黄沙铺出生,在黄沙铺长大,在我的记忆里,那是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但也是一个承载了太多苦难的地方。
母亲是一个性情刚烈的人,而父亲是一个性格温和的人。记忆中,总是母亲在保护着父亲,保护着我们。
文革初期,我也就5、6岁大小,到处都在造反,小镇上也未能幸免,曾是国民党某部少校军医主任的父亲更是不可幸免。每天,不是双手被绑在身后批斗,就是带着高帽挂着黑板在游街。记得,每次父亲被批斗回来,母亲总是小心翼翼的把高帽放在床架下面;每次要批斗之前,母亲总是将棉纱块包住父亲的双膝,再用绷带紧紧地固定好。有一次放学的路上,看到母亲也被绑着跟父亲一起游街,陪斗。母亲很胖,绳子勒在身上,一道一道的深痕,母亲没有抱怨,也没有跟父亲争吵。
有一件事情,我特别不想回忆,不想提起。但是回避,不等于它就没有发生过。这次送母亲的骨灰回黄沙铺,当地的老人感慨说,万医生真是一个大好人啊,就是文革时被整的太惨了,记得不?那时候万医生爬上了河堰边那个十几米高的水塔要自杀。
怎么会不记得,当时母亲派人急急忙忙的找到我,拉着我穿过人群,站在水塔下面。母亲朝父亲喊道,这是你最喜欢的小女儿,你舍得丢下她不管吗?县工作组的人对父亲说,没有什么事情是说不清楚的。
那么高的塔,一向文弱的父亲,是怎么一步一步爬上去的,他的心中究竟有多少的冤屈啊,让他以命相搏。
后来听父亲说,造反派天天逼他写出所谓“特务”名单,并且还圈定了几个人选,都是父亲认识的好人。父亲说,他宁死,也不愿意将无辜的人拖向深渊。
记得不久后的一天,母亲牵着我的手,站在山坡下面,对着上面的中医诊所破口大骂,那里住着几个闹腾得最凶的造反派头头,为了争这个院长,把我父亲往死里整。
一场文革撕开了人性之恶,礼义廉耻早已抛之脑后。男男女女、老老少少的都可以对一位德高望重的医生直呼其名,万同,万同的叫着。一天,母亲气势汹汹地吼道:“万同,万同,是你们叫的吗?他现在改名了,叫万爹”。
父亲慢慢恢复了工作,但二哥却失学了。整不倒父亲,他们就开始整子女。镇上的黄沙中学是读不成了,好心的村民将二哥接到孟垅的耕中去上学。二哥每星期回来一次,走时,再带足一周的吃穿用度。到现在,我还记得,母亲每次都会牵着我站在田埂上,看着二哥背着布袋的身影越来越远,越来越小,才会抹着泪,依依不舍的离开。
在一个天气还有些寒冷的夜晚,母亲打着手电筒,牵着我找到了贫农代表赵织锦的家,她当时是县委委员,说话很有分量。记得,她当时正在灶膛前烧着火,母亲蹲下身子跟她说了些什么,我早不记得了,但我一直记得,炉火印照下,母亲脸上谦卑的笑。二哥又重新回到了黄沙中学。
母亲最放心不下的还是做女儿的我,每到寒暑假,她就把我送到外婆那里,要我多开拓眼界,多看看外面的世界、多接触外面的人。母亲最喜欢打扮的也是做女儿的我。母亲十分能干,每次去武汉,总是带回很多各种颜色的毛线,各种好看的布料,有花棉布,有的确凉,还有涤卡。母亲亲手为我裁剪、缝制棉袄、罩衣,式样还很新颖。下班以后,母亲的手从来就没有停下来过,一边跟人拉着家常,一边双手织着毛衣毛裤,还穿插着各种花样。
文革后期,生活开始趋于平静,母亲又开始跟父亲争吵,要离开黄沙。武汉是回不去了,但是一定要调到县里去。二哥这时已经是县文工团的一名演员了。
父亲好像在黄沙扎了根式的,不为所动。他是真的跟当地的农民们建立了感情,有的农民看病钱不够,他会垫上;有的农户家里人得了急症,他会深更半夜挎着药箱去出诊。父亲的医术更是了得,在那缺医少药的年代,他硬是靠自己扎实的视、触、叩、听技术对一个又一个的疑难危重病例作出正确的诊断,救人无数。黄沙铺的老人曾对我说,虽然你现在也是一个名医,但你父亲在黄沙人的心中却是一座高山,没有人能够翻越过去。
虽然父亲并不想离开黄沙,但耐不住母亲每日里的争吵。调去县城,和儿子在一起,这个理由也足够充分。父亲硬着头皮找了区里的领导,又找了县卫生局的领导,事情慢慢有了一点眉目。
不幸的是,外婆得了牙龈癌,每天不能吃不能喝,疼痛难忍。母亲把她从武汉接到了黄沙,好在我们家就住在医院里面,治疗用药都十分方便,一段时日后,外婆还是离开了我们。
父亲亲自为外婆选择了墓地,在医院后面一个向阳的山坡上,背靠山,面对田野;田野很开阔,插秧时节满眼碧绿,收获时节又满眼金黄;田野中还有一条宽阔的河流穿过,远处是隐隐约约的山峦。母亲一直想离开黄沙铺回武汉陪着自己的母亲,未曾想却让自己的母亲永远地留在了黄沙铺。
意外总是一个接着一个。
有一天的夜晚,学校组织我们宣传队的人员到梅田茶厂观看地区文工团的演出,观摩学习,演出结束后就住在了茶厂。凌晨时分,听到有救护车的呜鸣声穿过,早晨起来,我们都猜是哪里发生了什么事情。当我们一路欢歌笑语回到黄沙铺镇的时候,突然看到卫生院门口挤满了人,眼尖的人看见了我,一把把我拉了过去,“你爸爸快不行了”。
见到父亲时,他已经昏迷了,也许是操劳过度,也许是旧伤复发,最后说是蛛网膜下腔出血。在外婆去世一个多月后,父亲也离我们而去,葬在了他亲自为外婆选的那片墓地上。
下葬的那天,四面八方的农民举着花圈自发的赶了过来,黑压压,到处都是人,出殡时,天上突然下起了大雨,棺木要上山时,雨突然就停了,这一自然现象渐渐地被神化。父亲,也成为了当地的一个传说。
父亲走时,口袋了装着一份调令。
父亲是11月离开的我们,我和母亲12月离开了黄沙。
母亲是一个要强的人,她见不得别人对我们施以同情,特别忌讳别人说我们是孤儿寡母,她开始冷静地分析形势,做出了一个明智却又让她后悔半生的决定。
1976年1月的某天,我正在县一中高二的教室里上课,大哥在教室外面打着手势让我出去,出门后,他就带着我来到了县委大楼,懵懵懂懂中,就办理了顶职手续,还没满15岁的我和母亲一起进入了通羊镇卫生院。母亲告诉我,如果我半年以后高中毕业就要下放,父亲走了,我们没有什么关系,到时候,推荐上大学、招工都不会有我的份,现在这样就有了保障。
这一决定,开启了我漫长的求学之路。
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医疗系统,有很多像我这种没有学历的年轻人充斥在各个岗位,除了不能做医生,什么技术岗位都可以做,就像工厂里的师傅带学徒一样,一个个野蛮地生长。
刚上班时,医院安排我坐在窗口里负责收费,虽然我年纪小,但我素来细心安静,日清月结,分毫不差。可我更羡慕穿着白大褂的护士,有技术。但医院里没有人愿意坐在收费室里动也不动,他们更喜欢病人少时聚在一起聊聊天,八卦一下东家长李家短。母亲看到我眼里那种求知的欲望,主动跟院领导提出来,跟我进行对换。从此后,母亲就离开了护士这个岗位,而我也成了病人口中那个打针不疼的小护士。
1977年恢复了高考,文教卫系统知青点的升学率很高,听说系统内组织知青们脱产复习了近一年。而我白天上班,晚上还要到医院参加政治学习,每天晚上十点以后才能看看书,没有老师,没有教材,时间永远不够分配。第一次高考,语文政治成绩很好,但数理化分数很低,第二次高考,数理化成绩上来了,但语文政治成绩又下去了,总是差那么十几分。有卫校联系我,是否愿意去读护士班,但当时的我,已经给自己树立了一个目标,那就是要做一个像父亲一样的医生。
1982年的中国百废待兴,人们的求知欲望空前高涨,各种职业教育应运而生。广播电视大学是一所覆盖面最广的学校,专业众多,教学方式灵活,深受在职人员的喜爱。在县城里,没有同学,缺少朋友,消息闭塞。当我知道电大有汉语言文学专业,也就是俗称的中文系时,已经错过了入学考试的时间,但得知只要每次期末考试合格,作为一名旁听生一样可以拿到毕业证后,我就在工作之余参加了电大的旁听,并以期末考试总分第一名的成绩拿到了毕业证,还结识了入学考试第一名的男生,也就是我现在的丈夫。拿到毕业证后,有一位行政单位的女领导有意向接纳我,可我依然有一个执念,要做一名医生。
机会总是降临给有准备的人。
1985年3月,通山卫校开办了一个面对在职人员的医士班,同时县委党校也开办了一个面对在职人员的公共管理班,都是脱产学习三年。这是一个身份转换的绝佳机会。但求学的路上,阻力重重。在医院像我这样没有学历的年轻人有6、7个,卫校的考前补习班时间已经过半,医院依然没有任何动静,母亲找了院长,院长认为人太多,不好平衡,所以不打算派人去学习。母亲又去找了县卫生局的领导,父亲曾经的下属,努力的结果是,医院把我们几个人召集在一起进行文化考试,我以第一名胜出,获得了参加全县考试的机会,最后又以全县第一名的成绩考进了卫校医士班。
电大的同学说我很奇葩,先读大专,后读中专。可他们不知道的是,我要的不是学历,而是医生这个职业,一个与父亲一脉相承的职业。
进入卫校以后,学习起来如饥食渴。跟我同坐的大姐说,你的成绩这么好,为什么不直接去考湖医咸宁分院和武汉市职工医学院呢?直到这时,我才知道有这样两所学校是可以招收在职职工的,同时也打听清楚了,这两所学校在县里的招生是有名额分配的,所以,打消了念头。
不久,武汉市职工医学院放开了招生名额,已经当了一年多医生的我又按捺不住,想要去报考。这次,医院领导直接就给否了。母亲又去找了卫生局的领导,也是父亲曾经的另一个下属,他亲自上门给院长做工作,最后给了我一个报考的机会。
母亲这样一个性格刚烈的人,为了能让我有上学的机会,一次又一次地去低头求人,我总自责是自己不够争气。可母亲常常懊悔,如果当年让我高中毕业后直接下放,也许早就大学毕业了。我常常安慰母亲,那也未必,我黄沙中学的同学,高中毕业后就下放到了茶厂,有的后来招工进了工厂,有的顶职后进了单位,也没有一个同学去读了大学,他们学习成绩也未必就不如我。
多年以后,当我担任了市中心医院儿科主任的时候,对那些想报考研究生的年轻人,我总是给他们创造条件。因为,在他们人生的十字路口,选择哪条路,将会改变他们今后的人生走向。
先生电大毕业后进入了县委办公室,1990年调到了当时的咸宁地委政研室,儿子这时已经上幼儿园中班了,我和先生都不在儿子的身边,儿子长期和母亲生活在一起,他习惯叫母亲为奶奶,而不是家家,一老一小在一起一呆就是两年。
儿子跟奶奶的感情很深,这种感情是日积月累、一点一滴相互渗透的。每次从学校回家,母亲总是会告诉我很多儿子的小故事。一次,她说有一天她感觉不舒服在沙发上躺了一会,等她醒时,身边围满了小板凳。儿子说,他打针的时候,奶奶是这样围着他的,怕他掉下来,所以,他也要这样围着奶奶,免得奶奶掉下来了。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我不在家的日子里,儿子生病,母亲从不告诉我,她一个人默默的承担着,只是为了我能安心的学习。一次,儿子悄悄的告诉我,有一个下雨天,路上特别滑,奶奶去幼儿园接他,结果,他和奶奶两个人都摔到地上去了,奶奶很胖,半天也爬不起来,身上疼了好几天。先生知道后,就开始让他在县农行工作的弟弟接送儿子上幼儿园。儿子是个懂得感恩的人,有一年电视上报道鄂州发大水,儿子很挂念已经调到鄂州去了的圆叔叔,他催促我们打电话,看看圆叔叔是否安全。
1992年以“学习成绩最优奖”从职医毕业后,我调入了地区人民医院,成为了一名儿科医生,结束了两地分居的生活,母亲和儿子一起来到了温泉。
4年后,我又有了报考同济医科大学研究生的念头,这时,儿子已经上小学三年级了,先生工作很忙,几乎不能顾家,回到家里也是一心研究他钟爱的向阳湖文化,经常写作到转钟。在我还在犹豫的时候,母亲鼓励我,想考就去考吧,只要是对的事情就要努力去做,她会好好的照顾儿子。
母亲这时已经快70岁了,但每天总是忙个不停,把我们的生活安排得妥妥帖帖,我总觉得母亲这样是不是太辛苦,母亲总是笑着说,你们好好工作、好好学习就可以了,自己退休了,不能跟社会做贡献了,能为子女们服务,子女们对社会的贡献就有了她的一份。
在同济医科大学的三年,又是母亲带着儿子一起生活。儿子有一次跟我吵架,说,我是奶奶带大的,你总是读书读书,爸爸总是出差出差。母亲总后悔,这是她的错,一步错,步步错。可我觉得任何选择都没有对错,生活本身就是一个不断修正的过程。
母亲总是觉得愧对子女,不断地想要弥补。大哥从小不在身边,缺少了一份父爱母爱,母亲想弥补。听说侄儿想从广东过来借读,母亲马上要求先生去联系鄂高,办理入学手续。二哥在文革中吃了很多的苦,母亲也想弥补。听说侄女快高考了,回家吃饭太晚,中午得不到休息,母亲马上叫他们中午都过来吃饭。每天一篮菜提上5楼,从不说一个累字。
母亲虽然显得很强势,但却是一个内心善良的人。我和先生来到温泉以后,渐渐地也事业有成,免不了有一些过去的老人、朋友、熟人找上门来,母亲已放下了过去,她总是跟我们说,要与人为善,能帮的就帮一把,大家生活都不容易。母亲帮人从不求回报。
随着孙子、孙女、外孙考上大学,母亲也一天比一天轻松,但人也一天一天老去。安静下来的时候,就喜欢回忆过去,渐渐地就变得絮絮叨叨的了。在母亲80岁的那一年,旅行社开展了一个“千名老人下江南”的活动。母亲说她一定要去,解放前,她随父亲一起去过江南一带,她很想旧地重游。我和二哥都没有时间陪同,很担心她的安全,但母亲执意要去,好在同行的老人中有母亲过去的老同事,还有一些低龄老人。母亲旅游回来后,特别高兴,不停地跟我们讲一路的所见所闻,这也是母亲生前的最后一次远行。
母亲虽然年事已高,但头脑却特别清醒,思维敏捷。一个人在家里时间呆长了,免不了孤独,母亲开始跟小区里的老人们玩起了麻将。那些站在母亲后面看牌的人说,母亲的牌打得贼精。那可能是母亲过得比较轻松的一段时光,上午看看报纸杂志,做一顿中餐,下午1点出门,5点回家,晚上开始雷打不动收看央视戏曲频道,用母亲的话说,既工作了,又娱乐了。但母亲有几天没有出去,我想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不愉快的事情。果然,几个老太太拌了几句嘴,有个老太太说,母亲总是赢,母亲不想争辩,懒得出去了。母亲跟我说着说着,还是有一点生气,她说打牌总是有输有赢的,我又不是出去送钱的,总是输,总是输,很光荣吗?智商低。生气归生气,过了几天,外面的老太太在楼下一按门铃,母亲就又出门了。
母亲年纪大了,我一直要请一个钟点工,但几次都被母亲否决了,她说,不习惯一个陌生人在眼前晃来晃去,一个人能动还是动一动的好,什么都不干,老得更快。在母亲85岁的时候,我执意请了一个钟点工,我的理由是,现在搬到了医院旁边的小区,到处都是医院的同事,看到你这么大年纪还提着菜篮子,是会戳我脊梁骨的。母亲无奈,只能接受。
母亲是一个讲究生活质量的人,过一天,就要有一天的生活品质。母亲在85岁的时候,做了白内障手术,成了眼科当时的明星病人,每天为眼科惧怕手术的高龄老人答疑解惑。母亲在90高龄的时候,意外摔了一跤,股骨颈骨折了,母亲又做了髋关节置换手术,术后第二天就推着助步器练习行走。母亲年纪大了,身体机能不断的出现各种问题,精神状态也有了一些异常。一生能干的母亲,看不惯钟点工干的活,而且,还慢慢变得多疑起来。在母亲出院后,我就辞退了钟点工,自己承担了所有的家务,希望母亲能过得舒心一点。广东的大哥大嫂知道后,赶过来照顾了母亲一段时间。
尽管母亲一生豁达、勤劳,看着身体状况还不错,但器官的功能正在不知不觉中衰退。
2021年11月的一个夜晚,母亲突然说着一些莫名其妙的话,明显的思维混乱。一大早,二哥二嫂和我们一起把母亲送到了市中心医院,但医院暂时没有单人病房,与市中医院联系后,我们赶往了市中医院。各项检查指标显示母亲的心、脑、肾功能已极度衰竭。中医院的医生护士们一直在不遗余力的进行着抢救,当天夜晚,母亲的呼吸心跳突然停止了,监护仪上显示一条直线。虽然母亲病危的消息,我及时告知了远在广东和北京的家人,但他们都还在赶回的路上。我当时只有一个念头,母亲现在不能死,她的孙辈们一个都不在身边。顾不得太多,我加入了抢救的队伍。母亲的命真大,呼吸心跳慢慢恢复了。第三天,母亲慢慢睁开眼睛的时候,床边叭满了人,母亲渐渐清醒,她认出了孙子、孙女、孙女婿、外孙,还有大儿子、大儿媳。
母亲病危时,医生预测大概只能维持十几天。二嫂是个做事十分利索之人,她赶忙上街做好了母亲的寿衣寿鞋,先生也急忙找人放大了母亲的黑白照片。
听着孙辈们一声声的叫着奶奶,母亲一天比一天清醒,情况一天比一天好转,母亲竟然活过来了,医生说,这是一个奇迹。
儿子看到母亲活过来以后,坚持要留在医院,一边写博士毕业论文,一边陪伴奶奶。这一留就是近三个月,直到北京出现新冠疫情,有随时封城的风险,才匆匆返程。
母亲已经可以扶着助步器正常活动了,但需要长期医养。母亲还是很坚决,不要陌生人的照顾。最后,还是按照母亲的意愿,让二嫂的妹妹过来照顾她。
二嫂曾经也是县文工团的演员,当年,她扮演刘三姐在小县城轰动一时,后来进入县政府的招待所做了一名经理,又后来调到市税务局成了一名公务员。母亲总说她是一个阿庆嫂式的人物。现在,我也这么认为。关于母亲百年之后,葬于何处?这需要一个答案,迫在眉睫,但我一直不知如何向母亲开口,母亲与黄沙铺有太多的纠结。二嫂怎么跟母亲聊起来的,我不清楚,但她告诉了我答案,葬在黄沙铺,和父亲、她的母亲在一起,命运真是捉弄人啊!
一天,母亲得知她在黄沙卫生院工作的老同事将从通山赶到温泉来看望她,十分高兴。她感慨道,他可是那个时候分来的大学生啊,长的很帅,最后还是在黄沙安了家。她说的帅叔叔,我知道,年轻时,操着一口江浙普通话,一副意气风发的样子。当帅叔叔出现在我面前的时候,已是满头白发,80多岁的老人了,同行的还有他的夫人和小儿子。
那天,他们聊了一上午,聊得最多的还是黄沙卫生院的一些往事。叔叔笑着问我,你知不知,当年,我可是被你爸爸“骗”到黄沙去的。叔叔跟我们讲起了当年的经历:我大学毕业后分配到了通山县,当时,卫生局的领导把我们这些大学生带到了一个大房间,里面坐着十几个人,领导说,这是各个镇卫生院的院长,你们愿意跟哪个院长走,自己选吧。我当时,一下就被你爸爸给吸引住了。你爸爸坐在那里,好有气质啊,一副高级知识分子的模样,衣服穿得笔挺。我想,有这样的院长,医院肯定差不了。到了黄沙铺一看,傻眼了,后悔都来不及了。那么偏僻、闭塞,连到县城的公路都没有,去一趟县里还要翻鸡口山。
母亲笑了,她说,你们去的时候条件已经改善了很多,父亲当年去创建卫生院的时候,鸡口山上还有土匪,父亲每次出诊,都有县大队的战士扛着枪陪同。那里,不仅有土匪,还有猛兽,母亲就曾经为一个跟老虎搏斗幸存下来的农民进行过包扎。
那天上午,他们聊了很多,叔叔还记得,他们那些从全国各地分来的大学生经常到我们家里去打牙祭。我也记得,有一次,雨后天晴,山上的野蘑菇蹭蹭地往外冒,母亲买回了很多的野蘑菇,然后,用猪肉(猪肉要票,父亲有特供,不受限制)、野蘑菇,加上辣椒,炖了满满的一大盆,香气在整个走廊上飘荡,他们都顺着香气寻来,围到了炭火旁,三下五除二,一下就风转残云了,可我还一点都没吃到呢。
叔叔还说到,父亲有几个宝贝。每年夏天的夜晚,父亲总是喜欢搬一把躺椅坐在院子里,旁边放着一部收音机。那是大哥自己动手组装的一台收音机,大哥从小就喜欢捣鼓各种电器,长大后还是成了一名电气工程师。母亲总是调侃我们三兄妹,男学工,女学医,花花公子学文艺。我也记得,父亲还有一个宝贝,那就是大哥从武汉给他带来的熊猫牌香烟,装在一个圆筒子的烟盒里,带过滤嘴。父亲舍不得抽,那些年轻的医生不时会向他讨要一根。
叔叔感慨说,万院长去世了,不久文革也结束了,慢慢地,各地分来的大学生也一个一个地走了,他也调到了县里。叔叔的夫人很能干,叔叔现在过的很幸福。
叔叔一家陪母亲吃完中饭离开后,母亲又是唏嘘了半天。母亲又跟我说起了父亲曾经的一件趣事。50年代山区条件艰苦,父亲经常挎着药箱出诊,有一次返回的时候,又饥又渴又累,正巧一辆吉普车从他身边驶过,父亲招了招手,吉普车停了下来,父亲坐了上去,吉普车把他送到了卫生院。父亲下车后才知道,坐在车上的是下来检查工作的张体学省长。
母亲的晚年是幸福的。虽然住在医院里,但每天有二嫂的妹妹陪着她,知冷知热;中午二哥二嫂总是开着车送去母亲喜欢吃的红烧肉、粉蒸肉、烧鱼块。我和先生每周都要抽时间过去,手上提的或水果,或肉圆。这样的日子持续了近一年,母亲还是要求出院回家。
2022年的9月,母亲回到了家里,最初生活一切如常。到了11月,母亲开始感到双腿无力,无法站立,跟母亲做了血液检查,没有发现什么特殊的异常,只能告诉母亲,这时人衰老的一个过程,母亲不得不接受这个过程,在家里坐上了轮椅进出。母亲习惯安排我们的生活,也安排自己的生活。她每天手机不离手,每过4个小时,就会唤我和二嫂的妹妹去扶她大小便。母亲的吞咽能力也在慢慢下降,如是,我开始调制各种粥食,有瘦肉粥、海参粥、皮蛋粥、青菜粥。这样的日子,也没有持续多久。
一场新冠病毒袭来,全家都未能幸免。母亲感染新冠后,不发烧,也不咳嗽,但慢慢地变得时而清醒,时而糊涂。最大的变化是,白天、夜间不停地要解手。母亲很胖,每次都要两个人才能抱起,夜间1-2个小时就要起来一次,常常是什么也没拉出来。一个月下来,我和先生已经是累得腰酸背痛,筋疲力尽。每当我上班时,二哥二嫂就过来帮忙,一天又一天的,他们也已感到体力不支。
侄女和儿子知道后,也十分的担心,担心我们也都是60多岁、70多岁的老人了。像这样劳累下去,还能撑多久?他们说要用科技改变生活,有的说要买瘫痪病人护理床,有的说要买瘫痪病人移位器。我在淘宝上搜索了一下,这些所谓的高科技,根本解决不了我们的问题。
日子还得一天一天的往下过,事情还得一件一件的来解决。母亲现在这种状况,来自于身体机能衰退引发的错觉。既要让她排大小便不受影响,又能让我们得到一点喘息的机会,不妨用成人尿不湿试一试。我跟母亲做好了工作,她同意穿上尿不湿,但就是不拉在尿不湿上,她说,不习惯把尿拉在身上。
有一天,我故意“威胁”母亲说,如果你总是这样不配合,那我只能把你送到养老院去。母亲把头一甩,骄傲的说,我是什么家庭啊?我不去养老院。母亲说这话时,底气足足的。她的底气来自于有三个儿女,来自于她心中秉承的母慈子必孝。可她忽略了一点,孝顺的子女有很多,可是能侍奉父母身边子女却很少。孝顺的成本很高,时间、精力、体力、财力,不是每个孝顺的子女都付得起。
渐渐的,母亲的情况越来越差,整夜整夜的睡不着,浑身疼痛,先生每过1-2个小时就要去给母亲翻身。那段时间,母亲一旦看不到先生就要问,大力士相公到哪里去了?救星到哪里去了?
慢慢的,针也打不进了,药也吞不下了,每天只能喝一点米汤、稀牛奶,意识又有点不太清醒了。大哥大嫂急忙从广东赶了过来,儿子下了火车听说奶奶情况不好,忍不住哭了起来。大哥大嫂回来后,看到母亲情况不好,就没有再离开。
最后一个月里,母亲好像已回到了从前,说的事,都是以前的事。提到的人,都是以前的人。有时候,突然问嫂子,“你爸爸有没有我这样的羽绒裤啊?他冷不冷啊?”;看见大哥二哥出去了,她告诉两位嫂子,两兄弟出去玩去了,她很开心的笑了。一会又问嫂子们,我姑娘呢?我亲生的姑娘呢?从小,母亲就把我养在身边,她总觉得女孩子容易被人欺负,她一直守着我,这一守就是六十多年。这六十多年里,我见证了母亲的苦难,为了丈夫,为了儿女,她受了太多的委屈。这六十多年里,我见证了母亲的幸福,她的愿望就是能让子女孙辈们受到良好的教育。这六十多年里,我见证了母亲的骄傲,她曾得意地说,你们这些博士、硕士、作家、医生、艺术家、企业家,都是我培养的。
母亲走得很有尊严。走的前几天,母亲躺在床上迷迷糊糊地说,我就从这里上岸。母亲走时,就像睡了一个长觉,身上干干净净,清清爽爽。
母亲还是又回到了黄沙铺,一个她一直要拼命离开的地方。一切早有安排,这可能就是逃不掉的宿命吧。
2023年5月9日写于温泉
作者:万致婷
编辑:zhufengjin
上一篇:
老岳母的“无字碑”
下一篇:
【彭红玉美文欣赏】余生只愿与你为伴
相关新闻
-
[朱封金谱学研究之五]连桐朱氏的前世今生

文公朱熹淳熙年间回婺源主持修谱时,为了有别于其他朱姓,把以茶院府君古僚为一世祖的本族定为婺源茶院朱氏,而在茶院府君的...
-
[朱封金谱学研究之五]连桐朱氏的前世今生

文公朱熹淳熙年间回婺源主持修谱时,为了有别于其他朱姓,把以茶院府君古僚为一世祖的本族定为婺源茶院朱氏,而在茶院府君的...
-
咸宁市温泉高级中学2020年秋季教师招聘公告
咸宁市温泉高级中学于2000年由市人民政府、市教育局批准成立,是面向全市招生、独立办学的市直公办普通高中。为适应我校教育...
-
扶志扶智 自强自立—— 嘉鱼激发脱贫内生动力

作为插花扶贫县, 2018年底,嘉鱼县建档立卡贫困户全部实现脱贫。那一年,因家大口阔而被评为贫困户的程贤功,通过仔细考察、...
-
咸宁市创建国家卫生城市简报第三十三期
城发集团对照整改清单,聚焦薄弱环节攻坚 2020年是我市国家卫生城市第二轮复审年,为做好本次的复审迎检工作,咸...
-
咸宁市创建国家卫生城市简报第三十一期
提升环境卫生保障能力持续改善城区市容市貌根据市政府关于印发《咸宁市国家卫生城市第二轮复审迎检工作方案的通知》,市环卫...
-
咸宁市创建国家卫生城市简报第二十九期
市商务局开展“固卫”工作专项督查行动8月24日上午,咸宁市商务局“固卫”工作专班工作人员在华信农批市场开展“固卫”工作专...
-
咸宁市创建国家卫生城市简报第二十八期

做实做细靠督导“创文固卫”见成效 为推进“创文固卫”工作有效落实,确保工作有序开展,根据《咸...
-
疫中值更•读春暖花开兼致海子
疫中值更读春暖花开兼致海子周春泉海子兄,真的面朝大海春天就会暖和起来么此时
-
中国网络文学产业规模持续扩大 近2000万写作者都是谁?
中新网客户端北京9月6日电(记者宋宇晟)从几年前的《琅琊榜》到去年的《庆余年》,再到今年关于网络文学作品版权以...
① 凡本网注明"来源:咸宁网"的所有作品,版权均属于咸宁网,未经本网授权不得转载、摘编或利用其它方式使用上述作品。已经本网授权使用作品的,应在授权范围内使用,并注明"来源:咸宁网"。违反上述声明者,本网将追究其相关法律责任。
②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咸宁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传递更多信息,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
③ 如因作品内容、版权和其它问题需要同本网联系的,请在30日内进行。

娱乐新闻
-
人艺“经典保留剧目恢复计划”开篇之作 《风雪夜归人》4月25...
 2025-03-27
2025-03-27
-
摘下神探滤镜 《黄雀》讲述充满“锅气”的人物和故事
 2025-03-27
2025-03-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