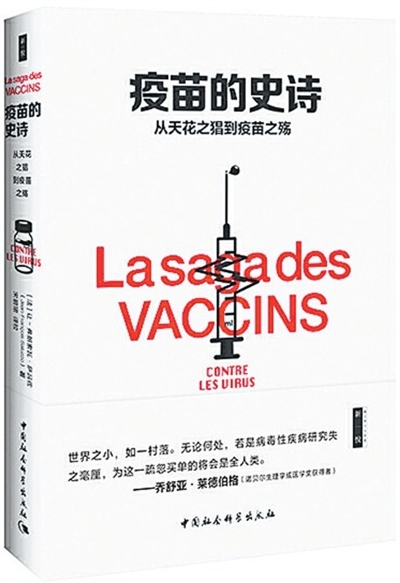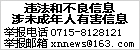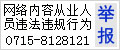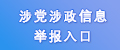相关新闻
-
我市累计接种新冠疫苗超100万剂次
记者了解到,市民接种疫苗的主动性很高,不少已经接种过疫苗的业主表示,接种疫苗之后感觉很安全、很安心,为自身健康提供安...
-
疾控专家解答新冠疫苗接种相关疑问
对于接种新冠病毒疫苗,市民还有不少疑问。针对这些问题, 5月23日,省疾控中心传防所计免部部长王雷进行了解答。记者:针对...
-
湖北不断优化服务满足疫苗接种需求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胡蔓龙华曾莉通讯员张春红郭霏5月23日,全省新冠病毒疫苗接种超过3000万剂次,全人群接种率稳步提高。据介绍...
-
中国国药新冠疫苗获世卫组织紧急使用认证

世界卫生组织7日宣布,由中国医药集团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研发的新冠灭活疫苗正式通过世卫组织紧急使用认证。它也是第一款携带...
-
湖北省新冠疫苗接种突破2000万剂次
5月6日上午10时40分,极目新闻从湖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获悉,截至5月5日,全省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2016.5324万剂次,最大...
-
单支两人份包装新冠疫苗将上市 省疾控中心:接种效果不受影响

5月7日, ,本周我省会有部分接种门诊收到两人份包装剂型新冠病毒疫苗,前往接种疫苗的居民可能会发现接种人员取出1支新冠疫苗...
-
三针疫苗vs两针疫苗!专家解答
首批“重组新型冠状病毒疫苗(CHO细胞)”现已在湖北投入使用成为灭活疫苗后又一款开放接种的疫苗这款疫苗的安全性如何?答:...
-
探访武汉“重组新冠病毒疫苗”注射,三针剂要这样打

极目新闻记者陈凌燕 通讯员刘翔首批重组新冠病毒疫苗(CHO细胞)已经在武汉投入使用, 4月20日,极目新闻记者来到汉阳区...
-
重组新冠疫苗安全性可以保证
近日,首批“重组新型冠状病毒疫苗(CHO细胞)”在湖北投入使用,成为灭活疫苗后又一款开放接种的疫苗。答:目前使用的重组新...
-
新冠疫苗不打第二针会怎样?有最佳间隔时间吗?最新回应
从前期新冠疫苗临床试验研究结果和使用时收集到的信息,新冠疫苗常见不良反应的发生情况与已广泛应用的其他疫苗基本类似。去...
① 凡本网注明"来源:咸宁网"的所有作品,版权均属于咸宁网,未经本网授权不得转载、摘编或利用其它方式使用上述作品。已经本网授权使用作品的,应在授权范围内使用,并注明"来源:咸宁网"。违反上述声明者,本网将追究其相关法律责任。
②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咸宁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传递更多信息,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
③ 如因作品内容、版权和其它问题需要同本网联系的,请在30日内进行。

娱乐新闻
-
人艺“经典保留剧目恢复计划”开篇之作 《风雪夜归人》4月25...
 2025-03-27
2025-03-27
-
摘下神探滤镜 《黄雀》讲述充满“锅气”的人物和故事
 2025-03-27
2025-03-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