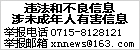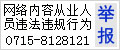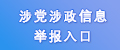舌尖上的年味
■方钰霆(嘉鱼)
年关将近,一晃在外已经多年,心头涌起许多思乡的愁绪,而过年这个老话题在心头涌起的都是温暖的记忆。在我的少年时期,过年占据了很大的分量,仿佛童年的所有期盼就是过年。大人盼栽田,小孩盼过年。这原本只是老家的一句口头语,现在却感觉格外的亲切真实。
小时候过年一般是从大雪开始,一旦开始下雪,大人们就忙碌起来,生在鱼米之乡,抽干鱼池的水抓鱼就是一件大事,鱼池在夏秋时是灌溉农田的水源,在过年时则是各家的鱼仓,一般年份好一点每家可以分个百八十斤,大部分都做成腊鱼。
还有一件大事就是杀年猪,用自家潲水和米糠喂养的,一年长个一百多斤不成问题,到那一天就是我们的节日,可以敞开嘴大块吃肉,在东北那叫吃“杀猪菜”,在我们江南则叫杀年猪,七大姑八大姨都来帮忙,然后围成一大桌,什么红烧肉、小炒肉、炒大肠等等,年猪肉的香味直到现在仍然记忆犹新。
当然,干鱼池、杀年猪都是大人们的事,我们最爱的还是各种小吃,虽然不是什么名贵的吃食,只需自己动动手就可以自己制作。进入腊月,围绕过年给小孩吃的零食便开始准备了,包括炸麻花、炸翻散、晒苕角、做麻糖等。
炸麻花、炸翻散比较简单,只需要到县城用小麦换一些面粉,回家后全家老少齐动手,和面的和面,搓麻花的搓麻花,烧火的烧火,一天的功夫就可以做上好多。晒苕角稍微麻烦一点,先要将红薯煮熟,然后把他煳在事先洗干净的麻布上,在太阳底下晒干,切成菱形即可。
做麻糖就很麻烦了,首先要熬糖,第一步当然是泡麦芽,用麦芽熬糖稀。一家人围着一口大锅乐呵呵地涎着脸,盼着锅里翻起的浪花快点凝结成糖饴,也好先入口为快。用大大的锅铲捞起浓稠的糖饴,看那流动的线条,确定灶膛里该留什么样的火候。差不多了就盛出部分糖饴,直接往锅里倒入早就炒好的胖嘟嘟白花花的泡米。
除了熬糖切糖,准备其他的炒货吃食也是等同视之的隆重和热闹。炒泡米的时候,一定会一同炒些玉米、蚕豆、花生、苕角等干粮。这些吃食,花生数量较少,算得上过年吃食中的上品,一般不给小孩子任意搬弄,而只在有客人来时才端出来,这时倒可以趁机吃到一些。
过年里对孩子吃零食基本不加干涉,从除夕之夜起,那些准备已久的零食正式对孩子们开放。
有了这些精灵般的东西,孩子的小嘴总是没得闲着,早晨出去便不见了踪影,家人也不急着喊回来,反正口袋里装得满满的出去,定不会饿着。时常在暮色里赶回家,才发觉中间少了一餐,却奇怪怎么不觉得饿呢?本来是想趁过年多吃些鱼啊肉的,却不知不觉中被这些粗糙的零食占据了胃的大部分。
白花花的米糖,干翘翘的玉米,黄澄澄的苕角,放进嘴里得先用力嚼,过足了嚼头这股瘾,甘味才开始像泉水一样渗透开来。这些硬邦邦的吃食,大人们似乎并不在意,跟着他们到村里串门,常有主人端出一碗香甜的米酒让人品尝,这是父辈们的最爱,手工制作这种米酒也是妈妈们的拿手活儿。
年关临近,从人们的问候里渐渐察觉到淡淡的年味。对于已步入中年的我来说,年味就像一支接力棒传给了孩子。现在的孩子不再追求过年吃点什么,那些或许早已经麻木了舌尖上的味蕾,但在我的心里,永远还流淌着以舌尖味蕾为代表的年味。
编辑:但堂丹
相关新闻
-
消失的外婆湾
孩子们不亲近严肃的外公,只缠着外婆讨要糖果。一转眼,堂屋的八仙桌就摆上了外婆亲手做的逗嘴食:砂焙苕片、油炸苕丝、干煸...
-
摇晃在光阴里的筛子
袁玉英(通山)在所有的乡村物件中,筛子是庄稼人不可或缺的物件之一。筛子从远古走来,不仅承载乡村居家过日安生立命的日常事...
-
幕阜杨梅正当时
朱丽平(通山)要问家乡春末夏初吃什么水果,我想非枇杷与杨梅莫属了。绿荷短暂的历程中,荷叶时卷时舒,荷花日开夜合,相互映...
-
丑桃
有的桃子浑身长满了疙瘩,有的桃子一面是桃肉、一面是桃核,有的桃子长着鹰钩,有的桃子裂成两半……整体来说,就难找到几个...
-
包坨香满天
朱丽平(通山)如今我家吃包坨,有些像酒徒吃酒。儿时我对母亲养的猪没有好感,往往是猪在圈内发出胡吃海喝般畅快的“嘡 嘡”声...
-
草尖上的春天
■程应峰(温泉)走在街头,人潮涌动,空气中氤氲着嫩嫩的春天的气息。这声问,一下子牵动了我单调的思绪,让我回到了记忆中熟...
-
【改革开放40年·咸宁建市20年】谈发展·话变化 亲历者说系列...

创新社会中的全能型人才讲述人:汪永富(市教科院院长)在鄂南高中从事教学、行政工作21年后, 2016年,我调到市教科院工作。...
-
10年后最有出息的,是这5种孩子
-
让孩子自动自发地去学习
-
5岁前读完1000本书?掌握这些方法就不难了
① 凡本网注明"来源:咸宁网"的所有作品,版权均属于咸宁网,未经本网授权不得转载、摘编或利用其它方式使用上述作品。已经本网授权使用作品的,应在授权范围内使用,并注明"来源:咸宁网"。违反上述声明者,本网将追究其相关法律责任。
②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咸宁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传递更多信息,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
③ 如因作品内容、版权和其它问题需要同本网联系的,请在30日内进行。

娱乐新闻
-
人艺“经典保留剧目恢复计划”开篇之作 《风雪夜归人》4月25...
 2025-03-27
2025-03-27
-
摘下神探滤镜 《黄雀》讲述充满“锅气”的人物和故事
 2025-03-27
2025-03-27